昨夜好大的雨,雨打一片红,虽零落一地,但枝头仍繁。这便是那株三角梅。院子里,从我的童年长到青年的三角梅。
是故乡的四月。不同于林徽因笔下轻灵柔风、暖气袭人的人间四月天,我的家乡——一座被北纬25度标记的南方小城,记忆里儿时的四月天总是带着一股奔放的、急促的热气,但又不像夏天炎炎直白的暑气,四月天的热气是迂回的、被春雨的魂氤氲着的。
正当我在这顽皮的四月天里纠结穿短袖亦或是长衫时,爷爷院里的三角梅已骄傲地在枝头绽开。你可曾仔细观察过这种随处可见的花?它没有花苞,只三瓣叶子般的花瓣,从初生之时便是三瓣花翼然张开的模样。
只等南风一吹便徐徐展开,一夜之间指甲盖大小的红色“翅膀”便扑棱成花蝴蝶一般,呼朋引伴地停在枝头,用压倒性的暖色向绿叶宣示主权,中间的黄色花蕊——便是这蝶的皇冠。只不过我家这一株不是花色,而是玫红色的。
那也是一个四月,那个才上幼儿园的小女孩,不及爷爷的自行车高,话都说不全,只咿咿呀呀地站在一旁。爷爷提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笑脸盈盈地走进屋来。小女孩见状立马屁颠屁颠地拥上前去——
“爷爷,什么?好吃的!”女孩欣喜地叫着,两双豆豆眼直勾勾地盯着那红色塑料袋,嘟着嘴巴作出咀嚼状。
爷爷蹲下,把塑料袋轻放在一旁,一只手作势捏了捏女孩的娃娃脸。柔嫩和衰老,红润和蜡黄,在这一瞬间交织在一起,流淌出暖暖的爱意。爷爷随后笑道:“好吃鬼哦!擒到什么东西都要吃哦!”虽然带着浓重的乡音,但咿呀学语的女孩不会说却已心领神会。不等爷爷再开口,便转向那红色袋子,笨拙地手指纠缠着袋子口,意欲拆开看看。
爷爷也不说话,只握着孙女的小手,一点点扯开,“树!叶,叶子。”女孩见到袋子里的东西便脱口而出。
“对咯,崽崽,这是树,一棵会发花的树嘞。”爷爷一边说着,一边从柴火棚里拖出一个大花盆,铲子等工具在院子里也一应俱全。爷爷围着这株花树忙活了起来,小女孩也围着爷爷忙活了起来。一层沙土,透气又透水;一层花生枯(花生榨油剩下的残渣),肥沃可护苗;一坨原生土,护根好长大。一层又一层,这棵花树可算在这棵大花盆里安家了。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玩乐,在女孩忙活下,花盆四周尽是散土。可是爷爷从不认为是女孩在胡闹,总是静静地看着她,看着她慢慢地、不熟练地用小手堆砌只属于爷孙俩的秘密花园。“
人人都说这花命贱,好养活。干什么要这样子讲哦,好养活不是很好的吗?越是普通越是有它的好处哩!”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老人,不懂专业的园艺知识、更不了解什么科学育儿经,质朴如斯。可就是这一份难得的简单,繁茂了那一课花树,也撑起了小女孩纯真的童年。
仍旧是四月,爷爷中风,卧床不起。女孩已经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已经可以用笔写出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里带一个“凡”字,老师说那是“平凡”的“凡”。女孩也不懂所谓文字的含义,她只知道爷爷可能等不到她能够理解就要离开自己了。窗外的那株花树,她知道那是叫“三角梅”的树,三年的时间,那棵树已经亭亭玉立,绿叶映衬着红花,奋力地伸出枝条探出屋檐去抓住那一角阳光,可是阳光从不为单棵树停留。
八月,那个四月之后的八月。艳阳高照,檐下的三角梅不需要伸出枝条乞求就可以盼来阳光,很烈的日光。可是爷爷长眠了,病榻没拘住他,他永久地放开了手,数月的病痛折磨,褥子上满是流脓的血水。因此在女孩眼里,离开是爷爷的解脱,爷爷终于可以换一副康健的身体,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快乐地活着了,继续种他的花。真正的生离死别,是没有过多语言的。
十五年,那个八月之后的十五年。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那个院子,去到北方的一个城市求学。这个城市有女孩没见过的雪,但却没有熟悉的三角梅了。离开之后,故乡只剩冬夏,冬夏的院子是没有发花的。去年冬天因故去广州办事,有幸见到了花城的三角梅,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三角梅可以全年毫无顾忌地盛放,三角梅可以不只有玫红色。很美,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但已经不是童年里的那一株了。童年里的那一株,是平凡普通的,和我一样,和我的名字一样。“越是普通越有她的好处哩!”爷爷在玫红色的花瀑下,注视着我,坚定地说。
和三角梅一样,我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做一个简单平凡的人,一个快乐盛放的人,也“有好处哩”。内心的力量不假外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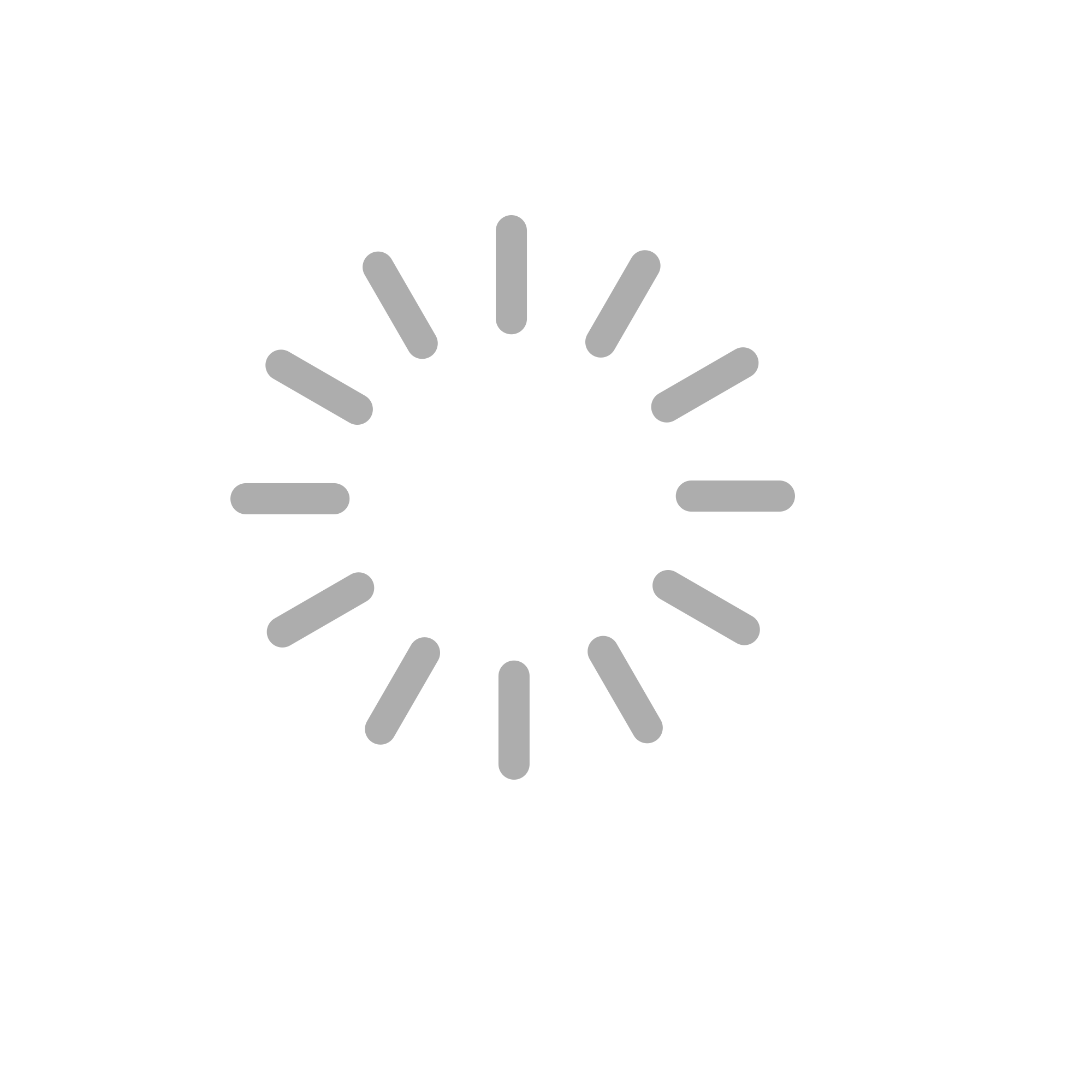
陈喜宝
短发过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