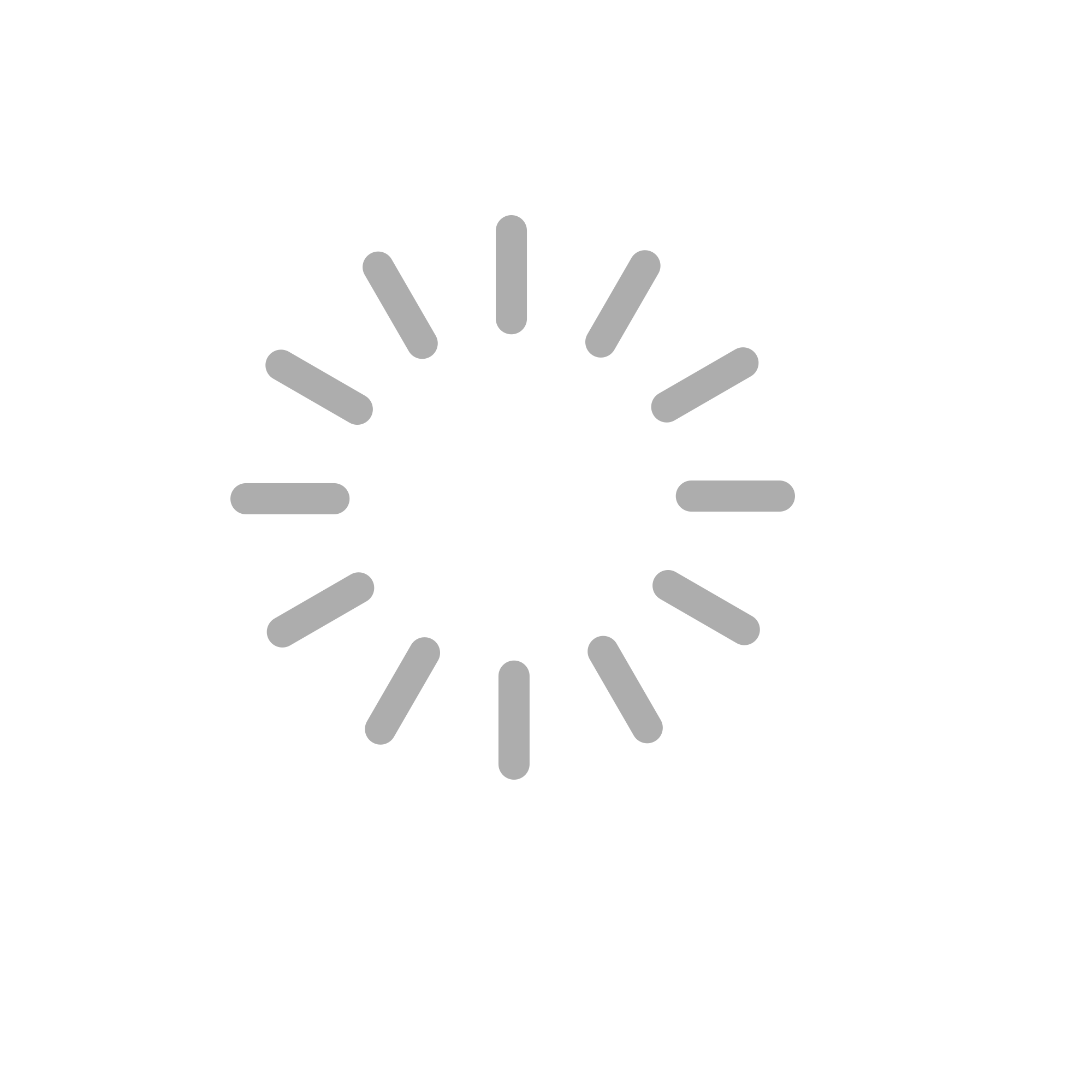因小时候一直住外婆家,于是大概就是我对爱情的启蒙吧,一个人是生活,两个人一起才是过日子啊。
如今二人依旧会每天上演这一幕对话中的你来我往,只不过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外公的烟瘾始终没戒,我爸责怪起时竟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抽烟呢我为什么不能抽?”如今住过一段医院后想必有所收敛,于是在厕所偷偷抽,但也因此总容易感冒发烧。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习惯也就渐渐一样,比如俩人午睡时总不爱脱外套上床盖被子,经常看见一人倚坐床头,另一人躺在床尾。
外公倔强,外婆随和,外公沉默寡言,外婆啰里吧嗦,外公的耳背也就只有外婆愿意多说两遍,外婆的万事通也就只有外公认真听,每次别人请客赴宴时外公总会搀着外婆走,俩人还有最萌身高差,也算是互补的典范了。
二、我最好的爷爷
我的爷爷据说是个十里八村挺出名的人物,至于为什么出名我也不太清楚,大多数人都只是说爷爷是个大善人,导致小时候我每次放学走回家时一路总能碰见一些爷爷们总会问我是不是xxx的孙女然后笑着跟我打招呼。
想必爷爷少年时家境些许富裕,在我年少时曾经见过时隔几十年之久的黑白老式照片,那个时候农村里还没几户人家有钱专请摄影师拍全家福。爷爷与其他兄弟三人并排齐坐前排,后排并站着妻子,身侧倚着几位其他人。照片里,每人都正襟危坐,背脊挺得笔直,一眼看上去就觉得正直万分,就像爷爷的一生,背脊从来都是直挺挺的,包括后来我儿时读书写字走路,我爸也总会拿挺直背脊说事。不得不说影响真的是潜移默化,导致我对男生的第一印象一直都是走路姿势。
去年,我在电视剧《白鹿原》里看了刘佩琦演的朱先生,那身上的一股劲,立马让我想起了爷爷,如果爷爷长袍加身,大概也会是这副模样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小时候的我每当一个人走夜路又或者放学路过坟墓时,心里总会想着爷爷,然后默默的背九九乘法表,真的特别管用!这个习惯哪怕是大半夜看完恐怖片我也会在临睡前不由自主的想爷爷背九九乘法表……
爷爷在我10岁那年胃癌去世,他待我从未有过重男轻女,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倒花露水洗澡、躺凉席上给我扇蒲扇,一直把我圈在里床不让我睡床沿,以致后来在阿姨家睡觉时阿姨说我晚上睡觉不安分到处东倒西歪,后来大了些,我一个人一张床有时会半夜掉地上,再后来,偶尔几次因故和别人拼床,我就一直睡在了床沿,睡觉安分了很多,却再没人在床沿守着我了。
在他还没生病时会骑着老式解放牌自行车接我放学,我坐在后座教他念26个字母,一路abcdefg回家,后来逐渐体力不支,便开始等我回家。我一路边走边玩总能走到天黑,头顶的天漆黑一片,点缀着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星星下面是向上伸张着的繁茂大树,顺着粗黑的枝干是透着暗黄灯光的小房子,一个人影倚在木门旁,屋内昏黄不清,照着的人影投在地上却很长很直。清夜无尘,月色如银,我总会小跑着奔进屋,然后喝下一大碗粥。
那张照片里特别明显的是左后方蓬头垢面的女人,我爸说,那是大爷爷的妻子,疯了。但大爷爷哪怕最后临终也一直未再娶,守着疯掉的大奶奶好多年。我对大奶奶的印象就只有这张照片里乱糟糟的头发与瞪着的双眼面目冷峻。对大爷爷的印象也就只有临终前中风住院的几面,那时,他已经在医院吸着氧口吐白沫了好多回,永远都闭着眼睛,却也依旧直挺挺的躺在病床上。右后方有一人也很显目,梳着漂亮贴合的发型没有一丝碎发,有着对比全照片最白的皮肤,眉形大概是修过的,静静的看着镜头,这是我的奶奶。我一直认为,奶奶大概年轻时是一户富裕人家的小姐吧,爱美,审美很好,哪怕现在是个老太太也依旧喜欢穿着碎花衣服梳个头型扎个头巾,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喜欢喝茶,在我狂热的羡慕橘子汽水时,她就给我喝椰子汁,不过椰子汁毕竟没有汽水喝起来爽,但现在想来,椰子汁应该属于那种唇齿回味的味道,而汽水等碳酸饮料不过是一时鼻喉膨胀的快感,总拉着给我抹雪花膏或者雪花棒,不过我特讨厌总是拔腿就跑,现如今早知道就乖乖让她给我抹脸了,总不至于丑到没脸见人了,长年如一日的做着养身操,小时候的我曾经跟在她后面做过几天,后来再没做过了,但她却坚持到现在,依旧每天对着墙上的养生操午休后做一遍,各种穴位按摩从头到脚来一遍,都快奔九的人了,皮肤还是比我白,除了脸上的皱纹外,一点都不像二十几岁的我一脸痘坑坑洼洼和黑头粗毛孔……
对于奶奶,我的感情有些复杂。她有些重男轻女,爷爷在世时我并没有太大感觉,但爷爷去世后,她常年在屋子里不待见我,也不大和我说话,我这才想起爷爷给我洗澡时她也只是在一旁自顾自的忙着什么,但她又是那个分屋后的一个雨天里跪在家门口台沿前哀求我爸妈允许病危的爷爷进大屋的人。爷爷病逝后,我们和奶奶的关系每况愈下,她再没进过我们大屋看爷爷的照片一眼,但每年清明又会折元宝;她会趁爸妈不在家悄悄的叫我去她屋里塞给我几个梨,又或者给我买过一次衣服,那年我差点被我妈扔进井里时也是她奋力的跑到我的面前紧紧的抓住我,但也是她说我害死了爷爷,并诅咒我不得好死,诅咒爸妈的晚年如她这般众叛亲离。她在晚年进行了一次人尽皆知的黄昏恋,我并不反对,我爸也并不反对,甚至让奶奶跟对方领个证以求在那户的子女面前有个保障,但她却破口大骂说我们不待见她。从不在家干活的她,却在那户人家忙东忙西,直至照顾那位老头子去世,最终被那户子女赶了回来。
也许,她在年轻时从未想过晚年的自己会是这副境况,她的一生无所出,但又不惜与爸妈决裂,也将姑姑的关系搞僵,与富裕的娘家人格格不入,最终只能奔走于政府村干部等第三人争取我爸的赡养费。她与我妈的关系不是没有过缓和,我爸也总会每年过年时偷偷的叫我给她送红包,我妈也是知道并默许的,但无一不是她接过钱关门大吉,歇停两天后继续每天搬个椅子坐在门口对着大屋咒骂。
如果说爷爷如朱先生搬拥有文人的傲骨,那么二爷爷就完全是一股当兵老革命的士气了。二爷爷一生从军,最后南下在福建成家立业,具体参加了哪些我从没过问,只知道二爷爷去世时当地市长等政府官员到场吊唁,全程都有拍照记录,所以由二奶奶整理并邮寄回来。我对二爷爷的印象就是瘦弱却刚硬的身板,走路也是笔直。二奶奶是个特别和蔼的人,小时候看《上错花轿嫁对郎》时,大概就是里面奶奶的模样,但更白净一些了。后来二爷爷一家开枝散叶,现在的全家福已经如一个班的阵仗了,从事着各行各业,但大多都已经是中流砥柱,名利与地位不说特别突出,但也是有几分薄面的人物。二爷爷还在世时,他会每隔五六年举家回来当做度假,儿时我的照片大概就是二姑姑给拍的了,那个时候的相机虽不说稀罕,但好歹农村里一排人家也是没有的。我爸说,早些时候的冬天家里还会下雪,二姑姑他们就会开心的在雪地里打滚。每次都会给我带礼物,不贵重,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很是新奇。后来,二爷爷去世,二奶奶年老腿不灵活,从我大学后便再也没有过来了。儿时的我总以为福建很远,远到恨不得漂洋过海跋山涉水,随着长大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格局如此之小。
其实亲戚里有钱或有权的人也有,富人越来越富,而我家却每况愈下。正如小时候他们回来二姑姑第一次给我拍照时那样,难免会胆怯、畏缩,倚在二姑姑的身边根本不会看镜头更不会拍姿势。但我爸却不这样,我觉得他是如二愣子般没心没肺,他对我说:有钱的我们比不上,也不去往上攀,要么你就怨你自己没本事,要么你就好好努力。也许当年要是有钱继续供我爸读书会更好,省得他时不时的翻我的书看见我写的名字横竖不够直就说我。
三、我那位拄着拐杖打人的亲爷爷
小时候总有一个哥哥指着我对我说:你本该姓仲的。后来这句话成为了那边大人们偶尔的打趣。
据说我的亲爷爷原先国民党,年轻时取了几房姨太太,爱好寻花问柳,最终瘸了腿落魄农村与原配奶奶和7个儿女过日子,期间把我爸送出去过继,先后贫富差距很大,经历种种特殊时期后,家境是更是拮据。印象里亲爷爷脾气特别不好,嘴上总是骂人,拄着拐杖动不动就抡起拐杖打人,我和他并不亲近,一来除了逢年过节外很少去,二来我从不踏进他的屋内根本不可能离他两米以内。
这边的亲戚们我都不大亲近,整个村子的氛围我都不太喜欢,领里互相背后喜欢议论别人,过年送礼什么的总给我感觉有些斤斤计较,男的有些畏首畏尾,女的又尖着嗓子说闲话。得亏是离我家的村里有些远,所以平日里并不需要过去。
四、我那一群鲜活的老年团们
近期有个打算,就是回家时用镜头记录下每张代表着时间的脸庞,嬉笑怒骂,老人也满是鲜活。
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小姨娘,从我有记忆以来,小姨娘永远都是满脸的笑意。爱笑的女生运气真的不会太差呀,小姨娘老来也是苦尽甘来,晚年无忧。小姨娘的笑,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笑脸,高中时有本书名叫《月牙儿》,便觉这是多么好听的名字呀,宛如小姨娘的一双混浊却月牙形的眼睛。儿时每见小姨娘,她总会弯着腰低下脸静静的看着我,那时我不爱叫人不喜张口说话,小姨娘总是一脸笑意的站在我的面前,待我妈推了推我从嘴里挤出话时,小姨娘总会提高嗓音应答一声“哎~”,然后摸摸我的脸才走向大人堆里谈笑。如今小姨娘的背果然弯了,但儿时面前笑意满脸的身影哪怕这时回想也依旧拥有一股鲜活的温暖。
第一次懵懂的知道人终将无声无息死去是在七八岁的时候,老婆(方言外婆的妈妈)躺在内屋,大人们都在前屋院子里安排后事,我不小心走错到了老婆的房间,老婆笑着慢慢的从枕头底下掏出手帕包着的冰糖给我,我拿来含着,老婆就又躺下,我却没意识到她已经说不了话了。我边走边吃,到院子里和表弟玩,天快黑的时候听大人们说老婆去世了。那时就只是觉得因为自己上学了忙了所以才看不到老婆了,后来渐渐长大发现这个世上已经再也没有一个大人给我吃好吃的冰糖了,后来让我妈买了两斤冰糖,吃了几块就懒得吃了。大人们偶尔会问我还记得不记得老婆,我默不作声,但每次手心握着几块冰糖却提醒着老婆鲜活的模样。
老婆喜爱戴一顶圆柱型的黑灰色帽子,比南瓜帽要圆且高,百度并没有找到我心中的帽型。老婆总爱戴着那顶帽子,穿着绣花鞋,坐在小屋的椅子上,手边倚着方桌,小屋背阳,到了下午就有些暗了,老婆也不开灯,黑色的帽子下显得脸色暗淡,一身的灰布衣,偶尔从门前望去,冷清得有些害怕。

绣花鞋
老婆的脚是三寸金莲脚,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漂亮小巧的绣花鞋是恐怖片的代名词,曾经老婆就将纳好的绣花鞋放在太阳下晒,巴掌大的鞋子,鞋头尖尖的稍有上翘,阳光下碎花的颜色红红绿绿煞是好看,但老婆从未让我见过她的那双脚,直至临终进棺,大人们谈起说起那双脚一阵唏嘘,却依旧没能看见,大概这双脚又记录着一段很长的故事吧。
去年末,我妈电话里说南边的某位叔叔终于没挨住冬天,在大年初消消的离世。如今的我妈,大概已经习惯了上一代们的离世,电话里的语气也听不到任何多余的话,只剩我继续细问到底是哪位叔叔。不曾想,明明上一年还鲜活的人,下一年就这么的再也见不到了,想了想,仿佛曾经捧了满手的干炒花生和瓜子,是他捧给我的。
老人们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们的人生正经历着最终的篇章,而正在老去的父母们竟也在不经意间紧跟着岁月的脚步往那个终点处集合,属于我这一代人的芳华渐渐落幕,侄子侄女们突然就这么落地奔跑。
不禁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罢了。
封图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