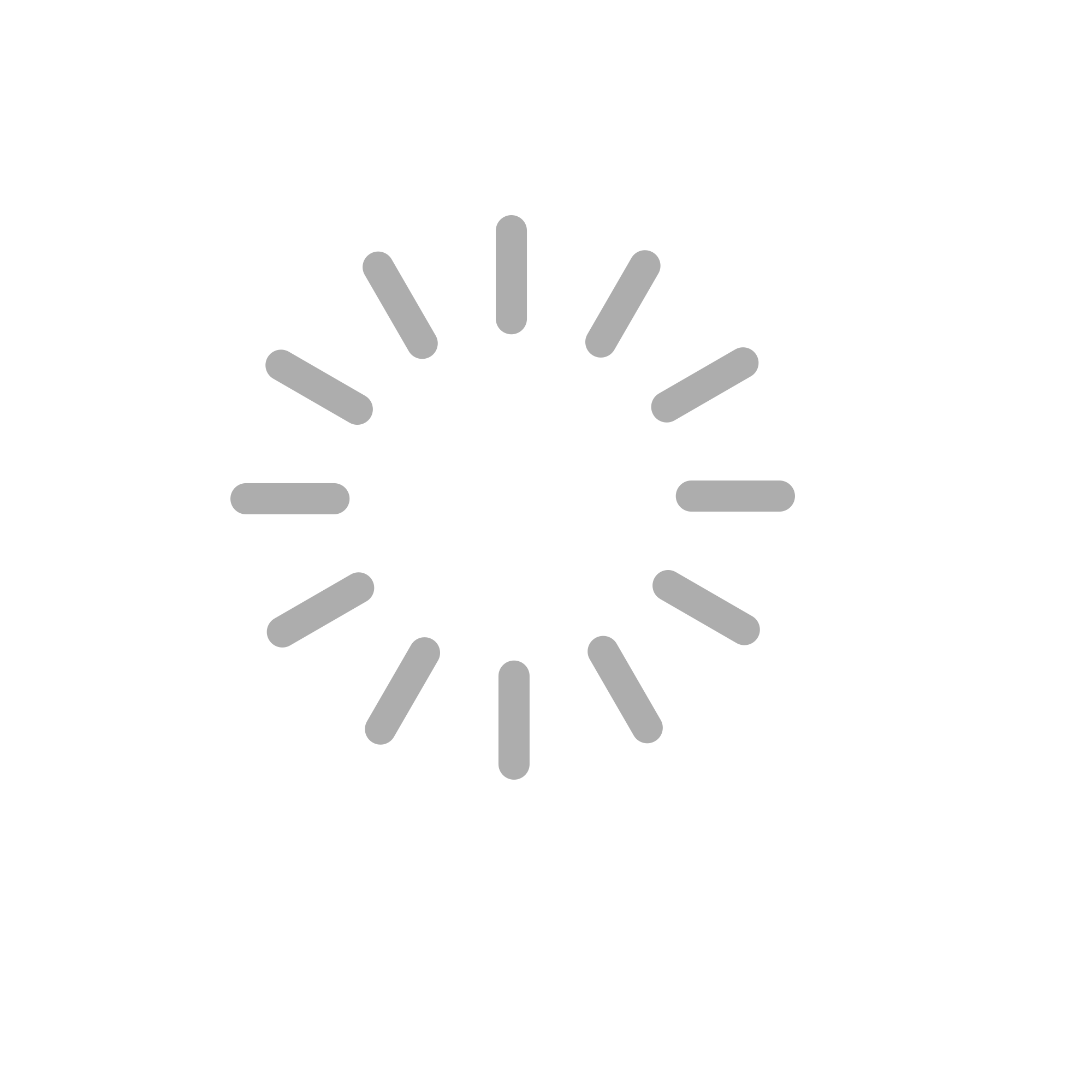感恩节的前一天,爷爷突然得知远在东北老家的大哥生了重病,大哥在电话里说,“别担心,我这岁数到了,病也该来了”,但爷爷还是慌张着让我订一张最早回东北的车票,嘴里不断念叨着大哥的名字,感慨自己离家60多年了,却很少回乡看看。
我问他这么多年想家吗,爷爷摸着光秃秃的脑袋点头说,“怎么会不想呢,但小时候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饥饿是我唯一的印记了,我和大哥那时候从来不知道饱是什么滋味。”
我们总是不能理解老一辈人为何像对待金子一样稀罕粮食,或许,在一位80多岁老人儿时的故事里,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母亲在流泪,我在滴血
七十年代,一位日本华人告诉我,日本的小孩子不吃糖了,糖已经吃够了;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今天,我也想自豪地告诉他,中国的孩子们也不吃糖了。
新时代下长大的孩子们,是在糖罐里泡大的;
我的孩儿时代,没见过糖,也不知道糖的味道。
图:饥荒年代 / 摄图网
我生活在充斥着饥饿和贫穷的大地上,那时候觉得自己活得还不如一头猪。现在都是牲畜吃人剩下的东西,但我小时候却捡了牲畜都不食的东西来垫肚子。曾听说过,在三十年代的东北抗日联军里有两位抗日英雄——杨靖宇和赵尚志,他们被日军围困在山上时弹尽绝粮,于是扯开袄子,嚼咽棉絮,又扒下树上干枯的树皮,费力啃咬。
人在饥饿的时候,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吃,也什么都能吃。我也吃过干树皮,还吃过杨树叶,槐树芽,榆树花…虽然没嚼过衣服里棉絮,但我吃过猪都不食的谷糠。
图:玉米粒和谷糠
谷糠是什么?稻谷脱粒成米,风扇吹过掉落下来的皮屑,便是谷糠。旧时有许多人家买不起棉花枕头,就用连饲料都作不了的谷糠当填充物,枕头用久见潮了,别人就把它扔在了院门外的角落里。母亲等人家回屋走远了,再把它捡回来,等一个天晴的日子铺在旧布上晒干,再用石墨把干碎的谷糠磨成粉末。
这些粉末尝起来干得直噎嗓子,想吐又吐不出来,想咽也咽不下去,母亲就往里面掺和了两把榆树皮粉,这混合在一起的粉末一遇水就变得又稠又黏的了,勉强能做成几个歪七硕八的糠团。等我们几个小萝卜头饿得忍不住了,母亲就把它们蒸熟了给我们掰着吃。这糠团吃在嘴里实在是没什么滋味,我就配着盐水,吃糠团。
谁想这糠团在我肚子里像一个发面馒头似的,把喝下去的水都给吸收了进去,卡在肠胃里动弹不得,让我肚子胀得什么也拉不出来,我那时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福气,饱了竟比饿着还难受。我的胃就像被犹如泰山一般重的巨石块压着一样,空气里也像是没了氧气,我痛苦绝望地哭喊着,既是因为这肚胀得实在难受,也是抱怨这喘息不得的生活。
母亲心疼得眼泪直流,她跑到屋外掰断了几根尖树枝,让我翘着屁股趴在铺上,用颤抖的手,一下、一下地,给我抠着糠粪。母亲在流泪,我在滴血。
我这一辈子,永远、永远,忘不了母亲给我抠糠粪的凄惨景象。
二、这两斤被雨水浸湿的米,掂起来沉甸甸的
冬季时候的北方,给人冻得骨头都麻木无力,呼吸中都夹杂着细碎的冰霜,土地也更是寸草不生,父母只能远去城里的人家做帮工,可赚来的粮食还远不够填满家里六口人的嘴,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只能在父母回村之前,去邻村讨点饭吃。
图:大雪覆盖下的农村房屋
那时我背着一个讨米用的破布口袋,一根打狗用的木棍,拖着饥肠辘辘的身子走家串户。冬日的黑夜来临得早,我就寻着有光亮有炊烟的人家,挨家挨户地讨。我走到农家大院门口,大声喊着:“大娘!大娘!给点饭吃吧!”,有好心的大娘会给我一捧米,我连忙拿布袋子兜着装起来,就连几颗不小心滑落到地上的米粒我也不会放过,昏暗的光亮里,我瞪着快饿昏了的小眼睛寻找着,用指甲扣着米粒拾起来,再忙立起身来,向大娘点头哈腰连喊着谢谢。
但有时也会遇到不怎么善意的太婆们,她们瘪嘴斜视着我,好像我的衣服都带着粪泥、呼吸都带着恶臭,生怕弄脏了她的大院,于是边扬手边回身赶着我走。我跪在地上带着哭腔哀求她:“行行好吧大娘,麻烦给我舀一碗米吃……”,她竟唤来了狗,吓得我本就饿得无力的身子更是站不起来,连滚带爬地仓皇出逃。在寒冷的天气里跑了这一下,胃里像有一股又冰又腥的血直往喉咙里冒,饿的感觉愈发难受了,眼睛和脑袋都变得昏沉恍惚了。
看见天色渐昏,大雨欲来,我心里想着天要变了,得赶紧继续讨了好回家,结果天仿佛听见了我的心里话,没好脾气地在半空里轰隆隆一句回答,天忽地像漏了一个大洞,雨水争相挤着从洞里泼撒了下来,没头没脑浇湿了我的全身,把我冻得整个人一下子全清醒了,让我清醒地感受饿的滋味,也让我清醒地体味苦的难熬。
图:瓢泼大雨 / unsplash
我只能找处有檐的空地,就这么一路带着雨水,哩哩啦啦走走停停,一晚上走了十几里路,只讨来了两斤米,这两斤被雨水浸湿的米,掂起来沉甸甸的。
三、娘!老鼠把那半块玉米馍给啃了
我曾因为饥饿,撒下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悔不当初的谎。我还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叫《半块玉米馍的故事》,刊登在了《湖北日报》农村版的报纸上。
农历二月的仲春时节,小巷旁的迎春花开的耀眼,花香在太阳的“烘焙”下浓得飘满了鼻腔,听城里人说这花的香味是淡淡的,但我却总是嗅出了具有植物气息的肉味。
谁想到当我走到家门外时,竟真有食物的香味飘来,我于是兴奋地跑进去唤着母亲。半块巴掌大小的、金黄蓬松的玉米馍就放在旁边的橱柜里。母亲正好从后院里进来,打算去外面捡些烧火用的木柴,她看见我正盯着橱柜里的玉米馍目不转睛,就走过来轻声跟我说,“那半块玉米馍是帮工的人家给的,你弟弟还太小,讨不到饭,就把这玉米馍给他留着吃吧。”

图:厨房里置物的橱柜
我的心情仿佛一架离手的纸飞机,刚升到了半空,转头碰了壁就垂头丧脑的掉落下来。我垂眼答应着,母亲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小脑袋,就出门拾柴火去了。
这时,我的肚子早已饿的咕咕直叫了,声音仿佛嗷嗷待哺的小奶狗。为了不让自己惦记那半块馍,我头也不抬的跑到铺上去睡觉,正午暖的我直犯困,索性睡一觉,睡着了就不饿了。
我在铺上翻来覆去,饿得腹背相贴,心里还是惦记橱柜里的馍,我睁开半只眼睛往那个方向抬眼眯着看,它正诱着我肚子的“小狗”。我鬼使神差地爬起床走过去,把那半块玉米馍捧在手里,它在手的温度下变得愈发香气扑鼻,我的眼睛里正冒着蓝光。

图:饥饿难耐
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把馍啃了两口,只啃了两小口,但本就不大的半块馍还是硬生生凹进去了一块。我既愧疚又害怕,就弄下些许的玉米渣和小半块玉米馍,放回了原处。
母亲拾柴回来了,我没底气的先发制人地说:“娘,我看见老鼠把那半块玉米馍给啃了!”,母亲似乎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心虚,她用那暖暖的、又无奈的眼光看着我,心知肚明地说:“你就把剩下的吃了吧。”听见母亲这样说,我还觉得她爽骂我两句才能抚平我内心的愧疚,我连忙摇头摆手地说,“还是留给弟弟吧。”

图:丰收的稻田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过去饥饿贫穷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家里的餐桌上鸡鸭鱼肉轮流转。但我依旧忘不了那半块玉米馍的味道,我内心的愧疚还是犹如年久翘边的纸张,怎么也抚不去,压不平,但这也反倒成了我忆苦思甜的宝藏。
儿孙总是无法忍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粮食的稀罕,只有真正受过饥饿折磨的人,才懂得感恩衣食富足的新时代,我更是贪婪得想再多活几年,享受这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的孙女如今也长得亭亭玉立,她从小就爱吃糖,我原来常牵着她的小手去车站旁的零食铺买糖。坐在铺旁的长椅上,我边给她剥着糖衣,边讲着玉米馍的故事。小丫头听得很入迷,丝毫没被来来往往的车辆给牵走了视线,眉头随着故事的情节忽而紧皱,忽而舒展。待我讲完后,她含着嘴里的糖果,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爷爷,这糖吃起来更甜了”。
受访人:陈秀才
整理人:家族事记编辑
图片来源:摄图网、包图网、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