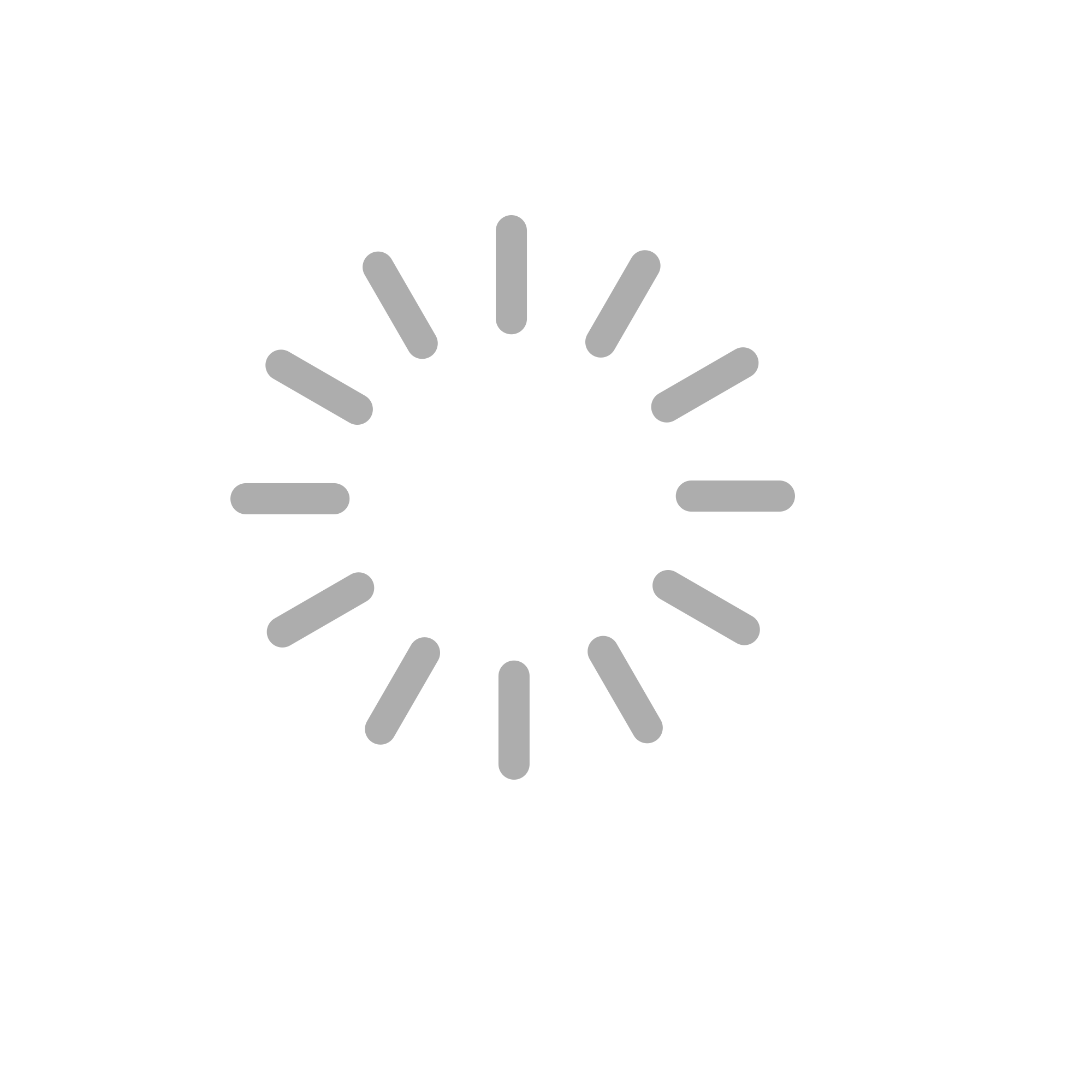作者:董夏

向德昙和《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张寒晖塑像
我出生在南方湖北省汉川县垸子台村外公向岩老先生家,外公75岁时才盼到他的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孩,欣喜异常,即用《左传》中的“美哉禹功,明德远矣”,给我取乳名为“美哉”,大名单字叫“夏”。
母亲向德昙幼年时和外公聚少离多,1927年,外公因不满蒋介石“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愤然辞职赋闲在家。百战归来的外公身板挺直,精神矍铄,着灰布袍,蹬青布鞋,更似一位教书先生。戎马一生的外公日常生活极有规律,闻鸡起舞,练拳健身,然后读报看书写文章。饭后躺在靠椅上,双腿盖条薄被稍事休息即可。外公智信佛学,44岁开始终身吃素,与家人分桌单独进餐,一日三餐,不外乎青菜、萝卜、豆腐、花生米、霉面筋、绿豆稀饭、米饭和面条等。
外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说:“我在外面革命了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只能让你们多读点书,以后的道路要靠你们自己走。”外公变卖垸子台的祖屋,送母亲进希理达女子中学读书(现武汉市25中),这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4年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武汉最好的女子学校。外公让自己的女儿读这样的洋学堂,足见老人家的开明和进步。
外公对子女严格要求,家里雇了位姓谢的老厨师,干活麻利,孩子们都乐见他。外公不喜欢儿女们养成衣来伸于、饭来张口的坏习惯,寒暑假在家时要求他们必须帮厨。外公每天晨练完后,来到孩子们房门前,用手杖在地上笃、笃、笃敲几下,转身离开。孩子们闻声即刻起床,自觉按功课表一丝不苟学习,随时接受外公的检查。母亲爱好练毛笔字,尤爱黑顿顿的颜体,据说,写这种字体的人刚强严肃,缺少幽默。但外公极力支持母亲练字,为她买了许多纸张。有一次,大舅看到了,顺口说了句:“德昙,你真有福气,爹爹给你买了这么多纸。”外公得知反问道:“你学画时,买的纸不是比这还要多吗?”大舅听了嘿嘿直傻笑。母亲在外公支持下,毛笔字愈写愈好。
外公更重视对子女人生价值和人格修养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外公根据自己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让子女们全部投奔共产党:继长子向浒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1937年又亲自送次子向仲豹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日军出动战机轰炸武汉,三婶张吉芝在她的回忆录《我的少年时代》中详细记载当时的情况:“市民们都在挖防空洞,学校也是如此,有时正在上课,突然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学生们赶快跑进洞去避难,警报解除后,尸骨遍地,血肉横飞,死伤民众不计其数,惨不忍賭……。”母亲从希理达中学毕业后作了一名教师,此时,有钱的人家跑到鄂西、四川避难,一般的家庭也去乡下投亲靠友,许多学生退学随着家庭转移,教室里的座位日渐空缺……目睹日寇的暴行,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22岁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她铭记父亲的教导,暗自下定决心:投笔从戒,报效国家。1937年9月,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我党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在应城汤池(湖北人称汤池为“小延安”)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时用名陶寒剑)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宗旨是培养抗日游击战争干部,正在武汉招收学员。母亲得到消息很受鼓舞,回家和外公、外婆商量。外婆担心她说:你哥和弟弟已经走了,你一个女孩子,外面兵荒马乱的叫我怎么放心?关键时刻还得由外公决定:“去吧,那个训练班是共产党办的,不会错。”

向德昙在汤池训练班(1937年)
母亲这期学员只有三四十人,条件差、生活苦,但师生们的积极性却很高。教育长陶铸平易近人,对每个学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周恩来、邓颖超还专程看望大家,作了重要讲话。母亲很兴奋,当天还照了一张相片珍藏至今,虽然岁月流逝照片发黄、影像模糊,依然可以看出她当年英姿焕发的风采。
经过短期的培训,母亲分配到十九路军,此时战事紧张,部队精编,老弱病残和女兵全部遣散。1938年的春末,母亲又回到武昌家里,她很惆怅:女子报国咋这难?此时,董必武正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常来我家做客,1937年外公秘密访问延安送次子向仲豹参加革命时和董老彻夜长谈的情形历历在目。董老很喜欢母亲,当他知道母亲在汤池已经接受过党的教育,就给母亲介绍许多关于延安的事情。在董老的启发下,母亲萌生了赴延安的念头。
但董老却对外公说:“少蒨兄,你的两个儿子已经参加革命了。德昙是家里的大孩子,武汉估计也要沦陷,年轻人全走了,您们一家老小怎么办?”
外公笑答:“国难当头,孩子们一定要走正路,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董老感慨地说:“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您一样,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1938年夏末,母亲带着董老亲笔介绍信出发了,外公对她说:“德昙,我不能像送仲豹那样送你去延安了,你一个人路上千万小心,要常给家里写信。”母亲乘火车沿平汉铁路北上,沿途难民成群,车上更是混乱,到信阳时母亲发现钱被偷了。聪明的母亲决定先在信阳住下,再写信回家要钱。1995年,我在湖北光化做客时,德曼姨曾说过一席话:“你妈当时多了个心眼,她怕回来后,外婆以此为由不让她去延安了。”不几天,母亲接到家中寄来的钱继续上路,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延安。
母亲带着董老的介绍信去抗大报到,并将名字改成“向捷”,寓意:抗战必胜,捷报频传。她见到了毛泽东,亲耳聆听了他的报告。1939年初,母亲从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凤翔东北竟存学校中学部任教,这是抗战初期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学校,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直接接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办事处不定期向学校派遣干部,学校前后接纳几千名东北流亡子弟,培养出许多党的干部和抗日骨干分子。著名教育家车向忱任校长,共产党员、音乐家张寒晖任教务主任。初创时,学校建在西安,1938年秋,日寇占领风陵渡,炮击潼关,空袭西安,学校迁至凤翔,中学部设在县城东关的城皇庙里。
1989年,表弟向虎雏来陕西渭南看望母亲,和母亲有过深入谈话。事后母亲告我:虎雏这次好像专门是为我怎样认识音乐家张寒晖而来的,还说我对抗战时期《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作出贡献。我告诉他,当时张寒晖对全国已经传唱的《松花江上》不甚满意,迟迟未定稿。贡献我谈不上,顶多起个作曲家面前“试唱者”的作用。
张寒晖,河北定县人,37岁,脸色微黄,尖下巴,戴副黑框近视镜,常轻微咳嗽,好像肺部不太好。他性格温和、待人谦诚,同时还兼授国语和音乐,母亲则教数学。当年母亲24岁,活泼好动,学校里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北方人,母亲是唯一的湖北人,满口浓重的南方方言,把“无”说成“冇”,“不”说成“莫”,“四”和“十”发音不清等等,北方人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母亲为此苦恼,故爱小声唱歌解闷,尤其是英文歌曲。
一次,张寒晖对母亲说:“向老师,你的歌唱得真好,尤其是女中音部,音域宽阔,圆润柔和,富寓情感。”
“张主任过奖了,我不过随便哼哼而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
张追问:“你家有人搞艺术吗?”
母亲答:“没有,但家父精心培养我,送我进武汉希理达女中学习了6年,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音乐是我校必修课,我还是校合唱团的成员。”
张听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并随即翻出几张写着简谱的纸,对母亲说:“向老师,这是我写的几首歌,请您斧正”
母亲接过来一边翻阅,一边轻声哼唱,当她看到《松花江上》的歌谱时说:“这首歌我极熟,前年在武汉就唱过,是你写的吗?”
张含笑点头称是,“我好像记得是佚名?”母亲不解地问道。
“署不署名并不重要,只要能对抗战起作用。谈谈您对这首歌的看法?”张豁然请求道。
“张主任,这首歌的词曲非常感人,不过我总觉得旋律太过悲伤。民众的痛苦有了,可是表现民众的斗争不足,日本鬼子靠泪水悲伤是赶不走的。曲调里如果增加些高亢的音符,更能激起斗志。我只是随便说说不知对否?”说完母亲看着他。
“我原来用的是北方女人传统的哭丧调,看来是有点太悲情了,不光你有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可是具体如何改法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张高兴地邀请母亲和他共同修改这首歌。

我没写过歌曲呀,充其量只能给你出出主意。”母亲谦让着。
“这就已经很好了,我看你的气质和学历,就相信你一定行。”张信心十足地鼓励道。
经过充分研讨,他们最后确定歌曲结构在原来二部曲式的基础上加上尾声、歌词应具有倾诉、叙述、抒情、号召力的方案。
第一部分仍保留传统哭丧调,便于叙事;第二部分的旋律用反复咏唱的方式,使情感愈来愈激动,用呼喊的音调,悲愤控诉日本鬼子入侵东三省的罪行;结束的尾声要唱出震天撼地的旋律,使歌曲达到高潮,以号召民众在悲痛中奋起反抗和斗争。
根据这个构思,他俩开始对歌曲进行全面改动,现成的乐器就是那架漏风的脚踩风琴,有些音还不准,只好因陋就简了。张觉得能和一位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合作会起到知识互补的作用,母亲认为能向一位有学识的兄长学习机会难得,后来他们发现对方都是工作态度严谨认真的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白天上课,利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他们对《松花江上》的词曲逐节逐段反复推敲,反复演唱……有时张说:“向老师,干脆按你对歌曲的理解自由发挥,我再找找感觉。”其他师生听到琴声和歌声主动围过来一起参唱,修改后反应效果更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竟存中学师生群众试唱实践,终于对歌曲满意了。张寒晖坐在风琴前看着写满音符的稿纸伸着懒腰,愜意地说:“向老师,我看可以作为终稿了。”接着他们又对张另外几首歌曲进行了整理,张寒晖把它们细心地誊写在几张纸上保存起来。
学校除了上课,业余生活单调。闲暇时,张寒晖或用风琴弹奏他喜爱的曲子,或用二胡演奏《江河水》《二泉映月》等曲子。母亲则演唱自己熟悉的英文歌曲,张说:“平日里难得听到外语歌曲,能在这偏僻的地方听到如此发音纯正的英语歌真是一种享受。”母亲成了他音乐创作上的得力助手。为了酬谢母亲,发了薪水,张提议请母亲去县城的小饭馆吃饭。母亲听后相当高兴,学校里的物质生活匮乏,师生同灶,一日三餐除了小米便是杂粮,南方人更是不习惯。张还约了几个同事,其中便有我的父亲,他也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北平大学中文系学生,临漳人,和张寒晖是河北老乡,且都曾在北京求过学,故走得较勤。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几碟家常炒菜,每人一碗面条对他们胜似珍馐佳肴。饭后,性格豪爽的母亲抢着买单,张说:“今天说好是我请客,哪能让你破费。”实在相持不下,母亲就说:“那下次我请客。”同桌的人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立即附议今后只要发了工资(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工资一律每月十元),就轮流请客。
后来,在张寒晖的撮合下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车向忱和张寒晖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母亲在东北竟存中学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半年后的1939年暑假,父母亲一同去了新四军豫鄂边区,临别时大伙互道珍重。母亲后来知道了张寒晖英年早逝的消息很是哀伤,她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兄长。

董夏和他的母亲向德昙
解放后,母亲在陕西从事教育工作,她淡泊地看待自己的革命经历,但当年的战友没有忘记她,她的名字收集在《中原女战士》书中。有学生问:“向老师,以您的经历应该是位领导干部呀。”母亲笑答:“如若那样,则多了个平庸领导,我的岗位就在学校。”母亲所在的瑞泉中学是陕西省级重点学校,还有两个班级曾经苏联英雄卓娅、舒拉的名字命名,当年这两位英雄的母亲访华时专程到瑞泉中学看望过学生们。母亲热爱教育工作,治学严谨,爱生如犊,长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她那一笔漂亮整齐的板书被学生们争相模仿,受到学生的尊重。学生们说:“向老师把数学中抽象的三角讲活了,能在脑中立起来,终生难忘。”学子们颂她:血汗洒三秦,学子盈四海,润桃李天下菲芳。
前几年,我去岐山出差,办完事情时间尚早,便对司机说:“咱们去趟凤翔吧,我在那儿有个心愿要还。”岐山距凤翔几十里地,汽车向西驶去,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凤翔县东关正街,我们沿路打问着来到了纸坊街12号竟存小学门前。1946年东北竟存中学停办、原址改为纸坊小学,1987年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继承和发扬竟存学校的光荣传统,决定将纸坊小学改为竟存小学,另在凤翔县城太北巷新建一所中学,命名为竟存中学。
这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早已和县城连成一片,学校正在上课,大门紧闭着,里面传来朗朗读书声,校门两旁栉比鳞次的店铺,街上的行人……看不出丝毫昔日的痕迹。
这里是母亲和张寒晖当年工作过的、不可移动的地方,发生过母亲与抗战流亡歌曲《松花江上》的故事。尽管沧桑巨変,人去物非,我还是思绪万千,眼眶忍不住充盈了泪花。
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