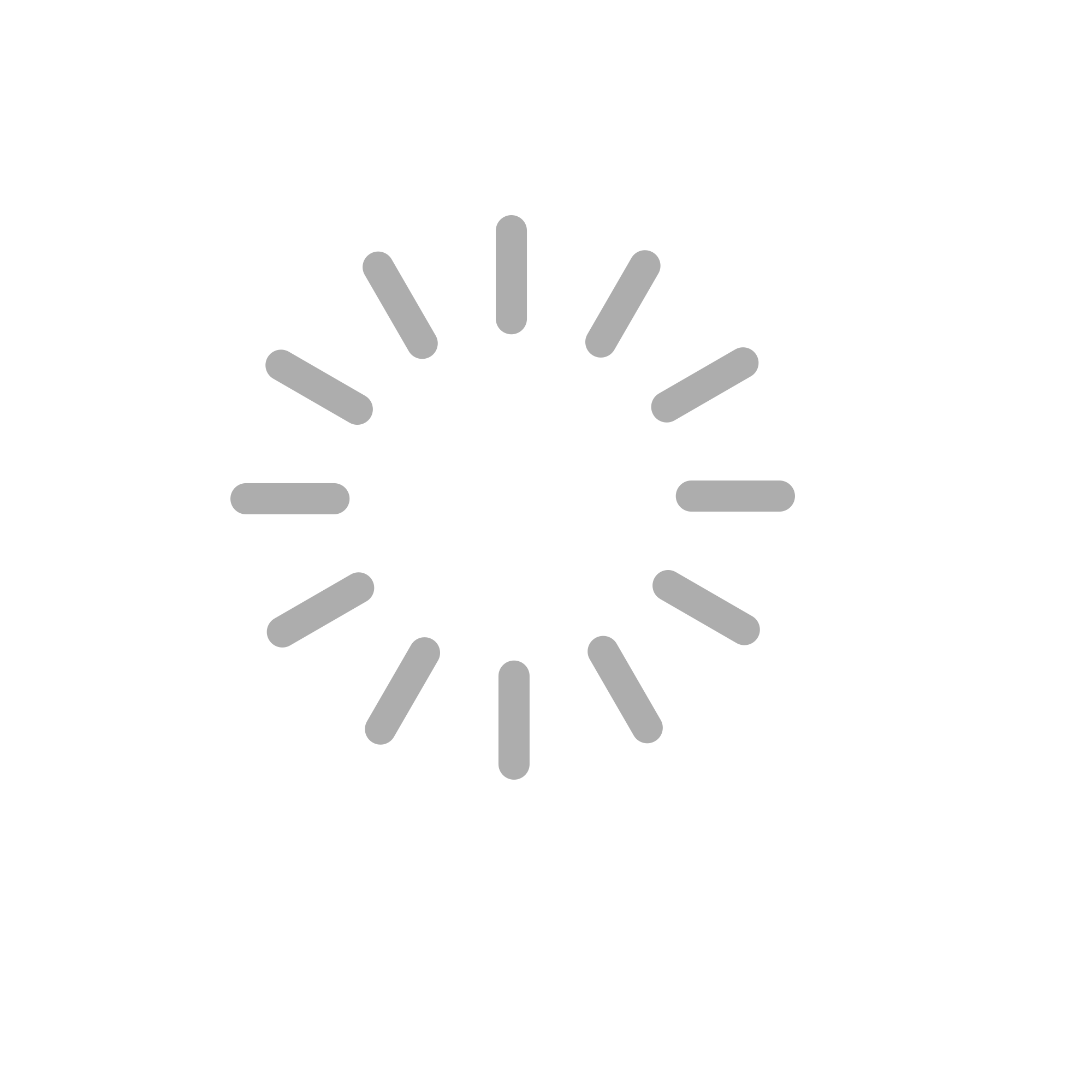老叔不高,应该有一米六,或许没有。前额挺宽,老叔嘘牛扬鞭驱犁,耕耘着岁月。岁月也在他额上犁下道道沟壑,从田间地头再到瓦屋陋舍快一个甲子。四季更换太快,营养跟不上的头发胡子花白,象深秋路边的草,没精气神儿。理成平头,阳光下倒有点反光。眼神贼亮,属聪明型的眼神,年轻时候精气神儿应该不错,笑起来亲亲切切。在乡下种地的时候,我和他的地相邻好几年,皆是种棉花。
那时候他六十岁不到,堂客比他小十岁,矮胖型的。堂客有什么穿什么,女儿、儿子不穿的旧袄子,女儿、儿子不穿的旧鞋。天气一冷,短的套一件,长的又套一件。半大孩子不戴的有耳朵皮革帽子,她说戴的真挡风、暖和,又不挂棉花壳,当然帽子小是小了点。堂客这样说的:“种地人嘛,穿的好有什么用,暖和就行。好衣服让棉花壳儿(棉花捡了后,剩的棉桃壳壳)挂糟了,还心疼。”所以相差十岁,看起来也差不多。这朴素作风是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作风。
七月半,一斤半。意思是到七月半,棉花脚下开始有烂棉桃脱了。叶茂,阳光照不到下面,棉桃爆不开。走到地头,就听见前面:嗯哼。那是老叔腰上系着棉花兜在找棉花桃,棉花兜是旧裤子或者蛇皮袋缝的。大概长年心中有释放不完的郁气,偶尔嗯哼一下,心中顺畅些。我说:“老叔,多早就来了,捡许多。”老叔回答:“嗯哼,没捡多少,捡一个少一个,老婶还没出门,在屋的慢慢摸,大白天的,不晓得摸么事,嗯哼……”
老叔棉花当然比我种的好,他的棉花枝上的棉桃各就各茬位,热热闹闹,一个不拉,按顺序密密排着队,象俏皮小孩探头探脑。我的棉枝上棉桃寂寞多了,丢三落四,旷工旷课的多了去了。老叔给自己抽便宜烟,给棉花吃好肥料,牛厩肥,棉籽饼,鸡屎灰,复混肥,浇粪水。从有机肥料到无机料肥,大把埋在泥土里,棉花脚边。天晴锄草,挑粪水,打药除虫,下雨清沟,整枝,地里打理的跟贤惠媳妇铺的床铺样,舒舒服服的。我说:“老叔,你棉花做的真好,你们好会做。”老叔应:“嗯哼,有么用,吃饭做饭混日子,一亩地最多两百斤皮棉,价格好卖千把元。也就四亩地,卖了,还还公粮上交(高峰时,一亩地还上交350元),去掉药水肥料钱,我夫妻两个天天劳作工夫不算钱,还要虫子口下留情,风调雨顺,也就剩点棉花杆做柴火,剩点棉籽油,我屋的床上棉絮象猪油渣样,冷天睡不暖,都不舍得打床新棉絮,嗯哼。”说的是,我一亩地就捡百把斤皮棉呢。聊一会儿,老婶趿拉着鞋子慢悠悠来了,鞋子长和身高比例悬殊大,不知谁的大鞋子,老婶是天塌下来,也不会三步并作两步的人。老叔眼角瞄瞄老婶,嘴巴尖嗫一下,一句嗯哼咽到肚里去了。老婶弯腰拔拉棉花杆,一心找烂棉桃去。
其实老叔是有故事的人,听他同辈人讲,二十几岁,他倾家所有讨房媳妇,他们夫妻关系还行,婆媳不对眼,吵一次之后,乡下人说吵破坝,口水就成洪水,决堤。三天两头吵,老叔又比较孝顺,他媳妇懒得逆来顺受,四方头巾一摊,放上换洗衣服,对角一系,拎着不声不响头也不回,回娘家去。还没生小孩呢,不留恋这个陌生的地方。
这一去,老叔守空房七八年,同龄人小孩都上学,唯他对影自怜,他也是很好面子的人,他干农活不比别人差。每到逢年过节,家家热热闹闹,他必在床上躺三天不起床,茶饭不思。他娘偷偷抹泪,也有些悔过,当年若忍忍,也不至于成这样。
老娘四处托人,说好话,成不成先拎半斤冰糖上门,说:“女的会蹲会站就行。”媒人就介绍现在的老婶,老婶矮矮胖胖,皮肤还白,也不丑。就欢天喜地办亲事,之后,生个女儿,一家人疼饱。谁知快三岁时,掉水塘里,老叔躺床上一礼拜起不来,心碎。之后,他养成毛恙,只要心堵,就躺床三天不想吃喝。好在,接着又生个女儿,把他们夫妻优点全集中,长的极标致,脸形五官无可挑剔,好大,那个奶奶还整天背着驮着不敢离手,之后又生两儿子,老叔的心终于放下,干活有劲,但偶尔郁闷时,还会迷糊两三天。
有次老叔和老婶扛上,老婶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个堂客多不好,当初就莫接我,当初还是我娘赖我同意,可怜你。”哦呵,话一出口,老叔也不吱声,径直往床上一躺,被单把头一蒙,那会儿天气还热,他不管。老婶也了解他,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地里干活。棉花地要撮坝儿,下午要抗旱,要紧的很,棉花渴的冒烟。要救棉花命呐,也是保证人生活所需柴火,棉籽油供应呢。下午她只能找别人帮忙一起抗旱,蛇皮袋里塞些稻草扎好口。水从地头过来,地里有几条地沟,就需要几个人抗旱,装了草的蛇皮袋放沟里,人站袋子上面,一边拦水,一边还得用粪瓢往棉花脚下舀水。水漫上棉花脚下的泥土才行,接着推着蛇皮袋往后退一段距离,站上去接着拦水,舀水。抗旱是统一实行,错过就错过,不会为你一家去安机子打水,水源有点距离。棉花正长棉桃,干旱严重将无收成,前功尽弃。老婶心急如焚也没办法,只能找别人帮忙。老叔是真躺的住,他的心又堵,多年的郁结习性。
老叔不干活就算了,一天到黑不沾饮食。老婶急的如热锅上蚂蚁,若老叔身体垮了,她更苦啵,是不是?老婶找老叔平时谈的来的乡亲,说:“哎哟,帮我去劝下我屋老的,不吃饭不行。”老婶其实也不错,她和老叔平时也都是不很会说话的人。
老叔的女儿二十出头,长大,就到南方打工,做衣服。女孩子很勤快干活,又不乱花钱,很体谅六十多岁的老爹,很照顾两个弟弟,月月工资千儿八百地往回寄,大家都知道老叔的女儿出息,知道老叔有钱。在地里边干活边聊天,我说老叔:“现在干活劲也足些吧,生个多能女儿。”老叔轻轻说:“嗯,得邓爷爷,享邓爷爷福哦。”口头禅重重的“嗯哼”,语调短,只剩“嗯”,重重的“哼”没了。有次我看见老叔的女儿从南方回来,确实惊艳我,如仙女下凡,仙气十足,偏又落落大方,见人就打招呼。我说:“女呀,你那多俏呢。”她说:“姐,那有你俏呢,你人美嘴更甜。”老叔老婶其貌不扬,乡下人说,破窑出好瓦,就是这个意思。
1998年,老叔女儿出嫁,男方江西人。老叔焉头搭脑,又不开心了。女儿是他的心肝宝贝,从没大声呵斥过。女儿说:“爹,莫难过,过年把呢,我在老家这边建房子,平时放假,过年,回黄梅。”说的他爹心又开,喜上眉梢。他乖乖女还真的说到做到,户口留在娘家,在娘家附近建房子居住,生小孩后,也叫她爹娘带。老叔开口闭口叫他外孙女:“我乖呐,我乖呐。”欢喜不得了。
我和老叔地相邻多年,我们和睦相处,锄完草,都要铲沟的,下雨好放水,棉花怕积水。我们好像惺惺相惜,都是把浮土铲上棉花脚边,不起相邻沟底雨后积泥。沟底泥是雨水冲积的,两边地都有份,有的人较劲铲沟,一不小心,地沟会把牛脚搞崴。有的在地头交界处栽上界枝(小型灌木)。有天发现,我和老叔相邻的沟,雨后积泥,被他们铲厚厚一层泥,这样他棉花地明显高些,我也惦记那沟里积泥呢,下不了面子铲嘛,他们家铲走就算了呗。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现在有的棉花地都起土变虾稻田,已桑田沧海,何处寻地沟?当年乡人经常为这个铲沟争的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男人会挥铁锹拗指头,快戳别人鼻子上,女人跺脚拍巴掌,快跺落裤,最后找中人拉绳子看看,界枝是不是还在沟中心。这个纠纷在国际上就是两国边界问题,不能小看,处理不好可能引发战争。有的尖刻乡民,总想铲别人的泥巴。
2002年之后,我在外打工,不种地。06年回家看见老叔,我说:“老叔,现在楼房盖了,又添孙,种田地又不用交公粮,现在有劲吧。”老叔边走路,脚下生风,边应:“嘿嘿嘿,是呵,胡主席晓得咱们农民可怜,不用交上交,做的收入都是自己的,嘿嘿嘿,好哦!”哦,老叔欢喜的忘“嗯哼”。
快八十岁时,老叔卧床好长时间,人生潮起已快潮落。有老婶耐心伺候他,他的孩子们放心在外打工,孙子孙女们老婶带着。老叔已无棱角支楞,穿衣、吃饭、擦洗,跟着老婶的步骤。太阳总是要偏西的,枕头也越垫越高,风摇残烛。老叔看着老婶不吱声,心里是感激的,回首倔劲往事,老叔有些愧疚,但心中无憾。
文章来源:公众号“乡音远方”